“乔云雀。”
许毅先开口打破沉寂,眼带好奇的问:“你应该念过书,什么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
乔云雀知道他想询问其他的,但她现在不想说话,只想干饭填饱肚子,拿着勺子舀了好几勺菜放碗里,嘴上说着:“先让我吃饱,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
许毅:“…好。”
她刚到部队家属院时,许毅是见过她的,当时像个毫无生机濒临破碎的傀儡娃娃任周母摆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死气,也不跟人说话,他了解她的身世情况后,对她也是有几分同情怜悯的,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可今天她却完全不一样了,人还是那个人,依旧瘦骨嶙峋,病弱得一阵风就能刮走,可精气神变了,身体里有了生机,双眼里不再灰败死寂,如今有了光彩活力,整个人像重新活了过来。
周斯年平时话不多,这下也没有开口,但他落在身上的眼神不容忽视。
乔云雀知道他们都是聪明人,也能感知到他们打量的眼神,但她一点都不担心,他们再精明也是普通人,绝不可能看透她身上的灵异变化。
至于她的性格,她病弱不常出门,常年呆在屋子里不外出,跟左右邻居亲戚都很少来往,在学校读书也很少跟同学接触说话,总是沉默寡言不吭声,同学也不敢跟她过多接触,怕她这个病秧子突然间倒地死了会赖上他们。
也就只有乔家夫妻了解她的性子,如今他们都相继患病去世了,周斯年他们就算去老家打听,他们也查不出异常来的。
他们三个将饭菜清空时,斜对面办公室里表演式的咆哮怒斥声也停歇了,只剩下杨晓媛委屈的痛哭声了。
紧接着,办公室的门从内打开,杨父阴沉着脸先出来,见外边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连护士台都没人值班,蹙了蹙眉头,瞟了周斯年的病房一眼,拉着一张脸走人了。
杨母紧随其后出来,也跟男人一样环顾一周,没见到人后,转身又进办公室揪着女儿揍了两下,覆在她耳边疾言厉色的说了几句什么。
他们一家三口像个小丑似的表演半天,可没有人捧场,也没脸再来周斯年病房,很快都灰溜溜的走了。
等外边的脚步声走远后,乔云雀放下了碗筷,没问杨家的事,开门见山跟许毅说话:“许副团长,你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许毅并不多问她的私事,只问事关周斯年的事,“你之前精神状态不好,有些事情不好问,现在你精神正常了,身体也有所好转,也是念了高中的知识分子,不知你怎么考虑自己和周副团长的婚姻问题?”
他是管思想政治工作的,跟周斯年同年入伍,两人关系很铁,一同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生死兄弟,许毅对他的个人问题也是很重视关心的。
周斯年各方面都很出挑优秀,深受领导赏识器重,不出意外的话,将来还可以在部队走很远。
许毅是打心眼里希望他好,不止在工作上,婚姻家庭上也希望他觅得合适的意中人,而这个被他妈塞来恶心人的乔云雀,真不适合他。
其实许毅对乔云雀也没有意见,相反因为她的经历对她抱以同情怜悯,今天接触过后,也挺欣赏她的志气性格,只是她的身体病得太重了,别说结婚照顾家庭生儿育女了,她恐怕都没法照顾好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
他心里想的都没说出来,但乔云雀想得到,也没有说破,神色如常的回答:“我和周副团长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一没相亲订婚办婚宴,二没向部队申请并政审登记,更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之间仅仅有的是救济恩情。”
她回答得清楚明白,这样的回答在许毅的意料之外,再次看她的眼神又变了变。
一直沉默的周斯年开口接了话:“云雀,以后不要再说救济的事,我家不省心的长辈给你造成了麻烦,也损害了你的名誉,本该由我代他们向你致歉。”
乔云雀身体如无骨人般慵懒的靠在墙上,脑子里想了些事情,坦诚直接的问他:“周副团长,你跟你父母关系如何?”
“为何问这个?”周斯年反问。
“如果你感念他们的养育恩情,你妈做的事,我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既往不咎。如果你跟周家关系不睦,那么我会做一些事情维护自己的权利名声,但我保证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前程。”
跟他们这些聪明人说话,乔云雀并不拐弯抹角,将自己的计划说得很直接:“我要向公安局、革会及妇联等单位举报,举报对象很多,罪名也很多,其中你妈侵犯我个人权益,变相买卖婚姻,违反了婚姻法,我可以此起诉她。”
她说话语速不急不缓,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晰,条理表达得很清楚,两个男同志此时看她的眼神都有些发亮,尤其是许毅。
见他们望着自己不说话,乔云雀微蹙着眉头:“我不能起诉吗?”
“没有。”
周斯年摇头,暗哑的嗓音很浑厚:“她的行为确实是变相买卖婚姻,我可以帮你作证,老家邻居及生产队干部也能作证,你可以向公安妇联等单位举报起诉。”
他的话也算是回答了之前的问题,他跟周家父母关系不好,不会感念周家的养育恩情,乔云雀不必看在他的面上既往不咎。
乔云雀也是个聪明人,明白他的意思了,点头:“好,我会处理好,不会让这事影响你。”
说完,想到现在的处境,只得再请求帮忙,“周副团长,我现在身无分文,也没有落脚之处,我还需要在你家里叨扰借住半个月,等我拿回被他们偷走的钱,我再付房租答谢。”
“是周家偷走了你的钱?”周斯年问她。
“不是。”
乔云雀摇头否认,并没有说其他的,讨要养父母积蓄的事,她打算过些日子亲自去讨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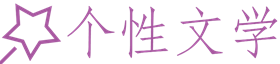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