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莺歌见阿绾也出来了,忍着将眼泪逼了回去,唯独一双眼眶还带着淡淡的红痕。
阿绾瞧出了她的不对劲,轻声问道:“莺歌这是怎么了?”
她抹了抹眼角,调笑道:“今日的风大了些迷人眼。”
对于这番说词,心下有些不信,那枝头的叶子并未凭风而动,哪里会迷人眼呢?
不过也没多做深究,扭头冲着黄川柏柔声道:“川柏大哥就先和莺歌坐会儿,菜马上就好了。”
“喝点茶水。”
谁知
等黄川柏去倒茶的时候,发现一壶都被喝光了。
少年阴恻恻的眸光掠过他,松风水月般的面容上带了几分不加掩饰的不悦,看上去没有什么,却有种逼人的压迫感。
还要留下来吃饭。
不若找点毒药,毒死这两烦心的人,落得清净。
黄川柏到底是久经沙场,一眼便能瞧出眼前这斯文风雅的少年不甚待见他们,眼角眉梢都是肃杀之意。
只是这平白无故的敌意让他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开口试探道:“不知公子可识南阳王。”
这少年与南阳王倒是有三分相似,早年听说南阳王妾室所生之子失踪了,今日看到他,才回想起来。
莫不是有所关联。
沈宴掀了掀眼皮,神色恹恹,讥讽道:“果然是官居四品的扬威将军,谈及的人都是些王侯将相。”
“不过在下只是个乡野之家,浑然不识您口中所提之人。”
果然一母同胞
生出来的也都是些性格相近的蠢货。
黄川柏面色一冷,目光投向一旁垂着头的黄莺歌,猜想方才定是拿着他的身份与这少年说了些什么。
才让他出言讥讽。
黄莺歌知道兄长有了些怒气,嗫嚅着不敢多做言语,将头垂的更低了。
只盼早些回去才好。
阿绾手脚麻利,做了几个小菜。
清汁田螺羹、细粉科头、清蒸鲈鱼、细粉素签,还有一味甜食梅子姜。
白瓷盘中佳肴冒着热气,丝丝缕缕闻着出乎意料的勾人食欲。
有了好菜却没有好酒。
黄川柏暂时将刚才的不愉快抛开,对着暗处扬声道:
“取点齐云清露来”
那人轻声应道,却不见踪迹,乃是豢养的暗卫。
齐云清露乃是上好的酒酿,酒香清洌而不艳俗,入口醇厚,千金难求,已是上品。
看着杯中清液,几人一饮而尽,入喉甘甜,却在五脏六腑中灼烧起来,慢慢侵入骨髓,整个人都酥麻了起来。
黄川柏挑了一块白嫩的鱼肉,肉质紧滑,鲜美异常,便忍不住舒展眉目夸奖道:“阿绾的手艺越发的好了。”
虽是家中常见的菜色,但胜在温馨二字。
周遭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壶清液也快喝见底了。
唯有沈宴喝的最多,一杯接着一杯,不曾吃过一口菜肴。
齐云清露虽口感甘甜,但酒性极烈。
早就染上了几分醉玉颓山之姿。
潋滟的长眸带着昳丽,似有水光攒动,唇色殷红。
美的雌雄莫辨。
阿绾也有些醉了,眼前有些模糊,但仍旧强忍着困意,对着黄川柏笑道:
“川柏大哥,日后有空再过来玩。”
“如今我在正华堂捡药,有什么事情也可说与我听。”
清丽的面容上带着柔和的笑意,温婉动人。
黄川柏忽的有些不想走了,但还是有礼貌的与她道别。
周遭的房舍屋瓦上洒落一层银白。
少女的身影被拉的很长。
门首悬挂着的灯笼闪着微弱的光芒,犹如飘浮空中的点点繁星,高悬在夜空中。
凉风习习,阿绾却醉了过去,趴在石凳上,口中轻轻嘟囔,不知在呓语些什么。
沈宴喝光杯中的最后一滴甘露,脚步虚浮的站起身来。
静立在月光下,清华出尘的面上泛着妖异的气息,脸上的笑意若有似无,落在少女粉嫩的耳垂上。
微眯的瞳眸有野兽捕食的光芒。
斯文风雅皆抛之脑后。
阿绾在昏睡中隐约觉得自己被人抱了起来,雪松般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沈宴身上的味道。
好闻。
她滚烫的脸无意识的在那怀抱中蹭了蹭,如娇弱的猫儿,引人垂怜。
怀抱紧了几分。
沈宴将她放与床榻,少女犹如初绽的新荷,羞答答的展示自己的柔美,紧闭的眼眸渗出几颗泪珠儿,挂在睫羽上,惑人至极。
冷白修长的手指落到少女微启的唇上,肆意的研磨,蹂躏。
一不小心就被含住了整根手指。
温热潮湿的触感袭来,丁香小舌轻轻的转动。
还以为是那什么解渴的冰块。
贝齿轻咬,酥酥麻麻自指尖流窜。
微红的小嘴不满的喃喃,“热”。
柔夷轻扯颈间的衣服,露出一小节精致圆润的锁骨。
殊不知落到旁人的耳中,是怎样的娇媚婉转。
沈宴的眼神愈发的暗沉,呼吸急促了几分,眼角眉梢都染了世俗的情欲。
绾娘是这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修长的手指落在那处锁骨之上,慢慢解开衣衫的活扣。
雪肤细滑,泛着淡淡的粉意。
乌黑的头发迤逦铺散开来,衬着如雪的肌肤,更添几分勾人。
想要将她弄哭。
沈宴伏下身子,轻轻地啃咬着那圆润的肩头,齿间生香,微微用力,便惹得一声嘤咛,宛转娇啼。
堪堪遮住的雪峰,如最纯净的圣洁之地。
他痴痴的笑了,眼尾上扬,勾魂摄魄。
暮地将其轻含。
绾娘只能是他的,也只能看他一人,今日盯了那旁人不知多少眼。
既然这样,就要受惩罚。
微微用力,引得少女不停的娇颤,泪珠儿更是接着一颗一颗的溢出。
莹白的脚趾都泛起了让人怜惜的微红。
沈宴看着那隐约的红痕,眼底含笑,将衣衫替她整理好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斯文清隽。
兔儿要慢慢的饲养,最后才能乖巧。
熟睡的阿绾只觉热潮迭起,做了一个活色生香的梦。
第二日起身洗漱之时,发现自己锁骨处的红痕有些讶异。
不知是不是喝多了,在哪里蹭上了。
涂了些胭脂水粉也遮不住,方才作罢。
选了一件高领的长裙穿上,才堪堪遮住那痕迹。
与沈宴作别之时望着那张风轻云淡的面容,却总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丝毫没有注意到那长眸中浮现的一抹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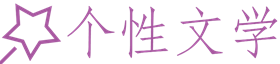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