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关了一整夜。
第二天午后,谢询才慢悠悠走进来。
他的额角被细致地包住,一看便出自女人的手。
看到我憔悴的模样,他脚下微微一顿,不过很快又恢复常态。
他施舍一般的,将食盒扔到我面前。
“李望舒,你若乖乖听话,也不会吃这么多苦头。”
他居高临下,成竹在胸。
也是,以往我们闹矛盾,总是我先服软。
今日他大概自觉给足了我面子,我便会欢喜地接下。
我仰头看他,有些茫然。
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人这么卑劣呢?
大概是眼中的失望太过明显,谢询逐渐察出不对来,脸上的笑挂不住了。
“你看什么?”他有些恼了。
我撇开脸,眨去眼底的涩意:“看狼心狗肺的负心汉。”
“谢询,你真不愧是春风楼的头牌,朝秦暮楚,处处留情……”
为了他,我背井离乡,市井里讨生活多年,很懂如何戳别人的痛处。
谢询的出身便是他的痛处。
这些年我从未提起。
如今,却也想让他尝尝我的痛。
但我没能说完。
气极的谢询一把将我按到墙上,咬牙切齿喊我的名字。
“李望舒,终于不装了?”
“无论江都还是京城,人人只知李娘子不知我谢询,我为了与你相配苦读七年,为什么成了探花郎还要看你的脸色?”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永远是春风楼卑贱的乐伎?”
他哑着嗓子:“李望舒,别以为我不敢休你。”
原来我多年心意,在他眼里竟是这样。
心被刺得生疼,我抬高下巴想啐他,却蓦然在他眼中看到了自己。
披头散发,面白如纸,口脂被胡乱地抹到脸侧。
难看极了。
狼狈极了。
我怎么……活成这样了?
我用力挣扎。
我不想哭,更不想看到这样的自己。
但谢询不允,他眼尾染上欲色,用力捏着我的下巴,逼迫我亲他。
“谢郎,”有人亲昵地唤他,随即惊呼,“呀!这是怎么了?”
谢询一怔,如梦初醒。
他慌张地看了我一眼,松开手:“文诗,你怎么来了?”
许文诗,谢询的青梅。
若不是那些信件,我竟不知谢询拿我的钱在三条街外置办了一处小宅,娇养了她五年。
他们一同搭葡萄架,一同放风筝,唱同一首歌谣,分食一碗白粥。
不能相见的日子,他们便寄情书信,待见了面,便将信件交换,作为日后聊天逗闷的情趣。
许文诗翩翩走来。
她今日一袭白衣,纤尘不染,这些年她未曾吃苦,模样娇憨动人。
明明……我们差不多年岁。
她绕过谢询,关切地伸出手:“姐姐,你没事吧?”
她笑得那样刺目,我突然觉得难堪,用力挥开她的手。
一天一夜没有吃喝的我并无多少力气,她却惊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很拙劣的表演,但因为有人宠爱,便肆无忌惮。
谢询果然慌了。
他疾步上前,一把将她揽入怀中,又狠狠将我往后推去。
花瓶碎片刺伤了我的掌心,我将他们瞧着,竟一时没觉出痛。
“谢郎,别怪姐姐……我知道姐姐还在为之前的事情记恨我。”
许文诗娇弱地流泪:“但我已为谢郎生下孩子,日后我们姐妹也是要一同在府中生活的……”
在她身后,一个酷似谢询的小姑娘咬着手指,好奇地看着我。
难怪。
难怪。
后面的话我听不太清了,强烈的窒息感将我吞没,我死死撑着地,没让自己倒下去。
“文诗!”谢询有些慌张地打断她,又看向我。
“是真的吗?”我抬眼看他。
“谢询,你早就打算好了,是吗?”
一阵难堪的沉默,他避开了我的目光。
夫妻数年,他的眼神并不难懂。
他承认了。
我垂下眼,后知后觉地感到痛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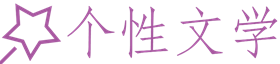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