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向财东立正,给陈孟之敬了个礼。
陈孟之挥了挥手。向财东跳上船,命令船老大:“起锚!”
船老大掌着舵轮,加大马力,在一阵隆隆的轰鸣声中,机帆船慢慢离开码头,吃力地朝上游驶去……
送走了向财东等人,陈孟之拄着棍子从码头走上街口,穿过槽门,在路边停留了片刻,朝街上走去。
烈日当头,街上的行人不多。两边店铺的摊贩们要么干坐在门口摇着蒲扇,要么放一把凉椅躺在荫凉处打着瞌睡。陈孟之一路走去,也没个人搭理。不知不觉就到了覃月月的裁缝铺外,犹豫一下,抬脚走进去。
覃月月背对着门,在案板上整理着一堆碎布料,听见身后有人轻轻咳嗽一声,回头一看,发现是陈孟之,有些意外:“你来做嘛?”
陈孟之也不见外,自己找个凳子坐下,手扶住棍子,望着覃月月,忧心忡忡地说:“你不晓得世道要变了吗?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了。石城,已危在旦夕!”
覃月月满不在乎,“我一个老百姓,既不是土匪恶霸,又不是政府要员,共军来了,又能拿我怎么样?”
陈孟之用棍子顿一下地,懊恼地说:“你这是妇人之见!这年头兵荒马乱,步步惊心,处处险境。就算他们不把你怎么样,可这非常时期,民不聊生,你一个女人势单力薄,能轻易度过难关吗?”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人一辈子,走什么样的路,过什么样的坎儿,那都是命中注定的。只要是个人,就得认命!”覃月月的话中明显带有一种情绪。她和陈孟之的关系,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白。
陈孟之急眼道:“糊涂!再怎么认命,也得看看是什么时候。现在,就不是任性的时候!”
覃月月眉眼一挑,挑衅地说道:“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跟你走?”
陈孟之也不否认,说:“这几天我都安排好了,专门征用了一艘船供县政府调遣。你收拾收拾,只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跟着一块儿走吧!”
覃月月冷笑:“哼,名不正,言不顺,我凭什么跟你走?”
一句话,倒把陈孟之给问住了。
覃月月说着气话,让陈孟之头都大了。
也难怪,一个女人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一个有家有室的男人纠缠在一起,熬到如今人老珠黄了,不仅无名无分,还常常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谁都会有几分怨气。加上这节骨眼上,陈孟之也没心思给她画饼,只是又用棍子顿了一下地,气恼地说:“别那么固执!这年头,能活命才是天大的道理,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哼哼一声,起身拄着拐棍,拂袖而去。
覃月月心绪烦乱,关上店门,进到里屋,坐在床沿独自发了一会楞,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红色的小布包,打开来,露出一只溜光闪亮的银手镯。她拿起银手镯端详了一会,目光渐渐变得有些迷漓。
提起她和陈孟之之间的情感往事,还得回到三十年前。
那一年,十五岁的覃月月和一个亲戚到省城长沙去玩,没想到半路两人居然走失了。可怜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省城举目无亲,又无处落脚,亲戚没找回来,口袋里的几十块盘缠却花光了。
覃月月想快点回家,可怜两手空空,急得在街边哭泣。忽然,有一个青年学生过来问她:“妹儿,你在这里哭什么呀?”覃月月听他说话的语气中带有一丝乡音,顿感亲切,就向他哭诉了原委,并取下手腕上一对做工精美的银手镯,恳求说:“这位哥哥,我真没钱回家了。这对手镯是我家祖传的,能不能押在你手上,给我借点盘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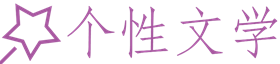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