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瑟的事儿太大,老奴不能不禀报了夫人。”
宁若虽有心理准备,此时也不免犯嘀咕:怎么这琴瑟出府了一趟,回没回来的,我还不知道,就变成了“事儿很大”了呢?
没等宁若说什么,应氏一听陈嬷嬷这话,也看了宁若一眼,也不赘言,径直转身往正厅回去了,还边走边说道:“嬷嬷来,我听着,让世子和小姐也听着。”
几人重新落座,甄宁若规规矩矩地坐了母亲右下手,默默地听着陈嬷嬷禀报。
“回禀夫人,今日一早,小姐差了人让老奴去她院中,说是因为琴瑟欺负小丫头,在院子里打架,当时小姐自己处理得妥妥当当的,让老奴很是信服。
老奴本以为,这只是件平常的小事,既是小姐处置了便也罢了,倒是小姐悄悄地和老奴讲,她觉得这琴瑟有些手脚不干净,但尚无把柄,不如先激一激,看这琴瑟有何表现,说不定三五日就能现出原形。
当时老奴心里还想着,这些个眼皮子浅的,也顶多就是偷些东西出去卖罢了,毕竟咱们府里对下人向来宽厚,犯了大错离了这里,他们得不偿失,不过正好咱们可以借机理一理府里的人情,也是好的。
老奴便按着小姐的吩咐,和冯管家那里说了一声,冯管家当即派了人,一直守着各门。
这琴瑟!还真如小姐所料,果真耐不住,下午就出了门。
她走的后门,拎着个包袱,守门的冬婆子竟然一句没问,也没查她,还笑呵呵地让她出了门,这差当的!
如今,老奴也先押下那冬婆子了。
而琴瑟出门,冯管家让悄悄跟着的小厮是车马房的石鼓,石鼓原还以为琴瑟会往当铺银楼去,他倒好抓她个现行,结果那琴瑟七转八弯的,进了离咱们侯府不远的一处小宅子,进去就不出来了。
石鼓差点耐不住,几乎就要走了,却见有个男子从那小宅子里出来了,鬼鬼祟祟地拎着之前琴瑟拎的那个包袱。
石鼓还算机灵,瞧着总是蹊跷,便又跟着这男子,却见这男子直奔往我们侯府来,还在咱们侯府大门口张头晃脑的。
石鼓觉得这人鬼祟,怕自己一个人看不住,便趁这人不注意,直接进府禀报了冯管家。
冯管家觉得这事儿太奇怪了,干脆自己到门口去问这男子。
唉,夫人,真是气人啊!
老奴后来听了冯管家的话,差点没气得背过气去,还好小姐及时发现,若不然,我们侯府的脸都被人丢尽了!”
陈嬷嬷说到这里,气得威严的老脸拉得老长,还愤愤地跺了几下脚。
应氏始终不动声色地听着,甄宁若看着母亲的脸,不禁也挺直了腰背,让自己压下满心的疑问,耐心地听着。
反而是甄英若,皱眉问道:“嬷嬷快说吧,到底怎么了?”
陈嬷嬷点着头,又道:“这男子和冯管家说,他想要见我们侯爷!冯管家斥责他,‘我们侯爷岂是你一个白丁好见的?你有什么事,若有要紧的,我帮你禀报。’
这男子支吾了半天,先是不肯讲,后来见实在没办法了,就又说要见夫人您。
冯管家便生气了,骂他不自量力,吓唬他说随意上门惊扰勋贵,可以报了官关押他,这人才有些急了,说他要说之事有关咱们侯府声誉,所以才要和侯爷或者夫人私下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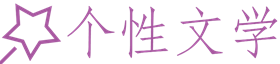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