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星沉满面嫌弃道:“胡振山那夯货一根肠子通到底,脑子从来不会拐弯儿,对栾亭又忠心得很,七八日没有消息,他怕是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在宫外既查不到栾亭的消息,进宫又见不到朕,定会按捺不住偷偷来探察一番,朕既然回来了,放他进来也无妨。”
倒不是长孙星沉真的料事如神,而是闯宫这种事,那厮前世已经做过一次了,当时闹得很大,被文臣们揪住了错处,差点被扣上“行刺皇帝”和“谋逆”这样的重罪。
他费了好大的功夫才保下这个杀才,为了平息此事,不得不下旨打了胡振山一顿板子,打得他半个月没下得来床。
傅英震惊道:“他竟敢如此胆大包天?这……皇上怎能纵容?!”
长孙星沉倒是不动如山:“朕都说了,他对栾亭忠心得很,为了栾亭的安危,他自然会向天借胆,什么都敢干。一个莽夫,跟他能计较出个什么?他又不敢行刺,只要看到栾亭一眼也就消停了,若不让他看一眼,说不定他做梦都梦见栾亭被朕施了一百零八道酷刑,正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傅英还是一脸不赞同,语气有些激动的道:“那也不能让他如此放肆,皇宫重地,岂能让他来去自如?若被他人知晓,天家威严何在?皇上的安危又将被置于何地?这种事绝不能轻纵啊皇上!”
长孙星沉安抚道:“所以朕让你给仇曲传个话,别把动静闹大,等他来了悄悄的骂他一顿,要打要罚都有道理,但一旦闹到人前,不狠狠收拾他都不行了。”
他见傅英还要说话,接着又道:“你安排一下,今晚朕要见孟清。”
傅英的注意力却没有那么容易被转移:“是,皇上。可是胡将军……”
长孙星沉脸一虎,沉声道:“没有可是,朕自有成算,你去传话就是了。”
傅英见皇帝面色不好,不敢再多话,只皱着眉头,不情不愿的应了声“是”。
长孙星沉这一个澡估摸着能洗掉二斤泥,水换了两桶,才得以一身清爽的走出偏殿,而他出来时,殷栾亭已经换了一身略显宽松的长袍等在外面的花厅里了。
他原本苍白的脸上被热气蒸出了几分薄红,看着气色好了些。只是换下了厚重的外袍,只着一身宽松的单衣,看起来身体瘦削得过分,半湿的长发披散着,显得下巴越发尖削了,整个人看起来就很不健康。
长孙星沉皱了皱眉,走上前去,缓缓坐到他的身边,放在扶手上的手指微微动了动,却没有想好要说些什么开场白。
殷栾亭一直半垂着眼睛坐着,颜色浅淡的薄唇轻抿着,看到皇帝过来也没有开口,更没有起身行礼的意思,说好听了是在“听候发落”,说难听了就是消极抵抗。
傅英看了看他们,笑容满面的上前道:“皇上和宁王殿下一路辛苦,想必也饿了,不如这就传膳吧,再有天大的事,用过膳再说也不迟。”
长孙星沉干咳了一声,摆手道:“说得对,传膳吧。吩咐御厨房,以后每日都做些滋补的汤品。”
傅英笑眯眯的道:“宁王殿下确实清瘦了许多,想必是平日多有操劳,累坏了身子。奴才该死,竟疏忽了,没有早早儿的备着。还是皇上细心,皇上与宁王殿下的深情厚谊,真真儿是羡煞旁人。奴才这就去传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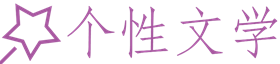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