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月怜是被疼醒的。
穿越前,她睡得是席梦思。
穿越后,她住的是凤栖宫。
从未在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睡着过。
身体上还有痛不欲生的酸楚,醒来时她的腰腿都不听使唤了。
房间依旧保持着狼藉的原貌,她宫廷定制的喜红色嫁衣被撕得破破烂烂躺在地上,那个盖头也皱皱巴巴的沾着一些东西。
姜月怜的脸比猴子的腚还红,恶狠狠瞪了眼那身喜服,裹着被子下地,一脚踩在喜服上。
似是还不够解气,用脚勾着喜服盖在盖头上,来来回回的踩踏,反反复复的碾压!
每动一下,都在强忍着那股被抽骨般的痛。
过了大概五分钟,姜月怜终于解气,一脚踢飞了嫁衣,踮着脚尖来到房门前,缓缓打开一道缝隙准备查看外面的情形。
脸才刚凑过去,一双眼睛就贴了过来,两人隔着一道门板无声对视。
姜月怜吓得差点就会说话了。
反手就把房门关上,后背紧贴着门板,呼哧带喘的平复心情。
张管家轻轻叩门:“夫人,相爷出门前已经吩咐老奴为夫人准备衣裳,就等夫人起床呢。”
姜月怜紧咬下唇闭上眼睛,一脸的灰败之色。
缓了缓,她重新用被子把自己包成了个粽子,才将房门打开。
张管家面带微笑,是昨晚姜月怜不曾见过的真笑。
“阿巴阿巴!”
姜月怜伸出手,朝他要衣裳。
张管家点头,扭头冲婢女道了句:“你们两个进去好生服侍夫人。”
“是。”
婢女还是昨晚那两位,反正都是一样的监视,比起香巧香茗来,倒是安静许多。
比她看起来还像个哑巴。
动作利索地换好衣衫,一名婢女便去唤张管家。
张管家甫一进门,就闻到满屋的甜稠。
再看看长椅上混乱的被褥,便是他三十年光棍一个,也约莫猜出昨晚发生了何事。
张管家略微诧异地看了眼姜月怜,随后恭谨地笑了起来。
“夫人可歇息好了?厨房已经备好了膳食,就等夫人一句话呢。”
姜月怜身心俱疲,早就饿的五脏六腑齐齐抗议。
更想要赶紧离开这大型社死的现场,慌忙点头,跑了出去。
张管家:“你们两个好生伺候着。”
婢女们应是,紧随姜月怜身后离开。
望着那道渐行渐远的婀娜身影,张管家眸色渐深。
主子身边有形形色色的女子流动,时间最长的从未超过仨月,便被阎王爷召唤而去。
别提能亲近主子床榻的人了。
这个姜月怜,好像真有几把刷子在身。
姜月怜回了望月阁,香巧和香茗见她能活着回来,都松了口气。
从谢府婢女手中接过姜月怜,香巧嘴甜地谢过两人,又塞了把金豆子,才将房门关好。
“夫人您可回来了,昨晚大人可有拿你怎样?”
香茗开门见山,问了一堆问题:“还有夫人昨晚睡在哪里?衣衫怎么换了?”
香巧用手肘推了一把香茗,翻了个白眼,“真想知道的话先去拿纸笔。”
香茗一时语塞,适才想起姜月怜是个哑子。
转身离去时背对着姜月怜,跟香巧使了个鄙弃的眼色。
跟着哑子做事,简直急死个人。
哪怕得到第一手消息,也不知道要何时才能问清,又猴年马月才能转告给皇后娘娘。
姜月怜真正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她身上的痕迹是藏不住的,香巧香茗两个定能察觉出不同。
皇后也能很快知晓。
目前皇后没给她下达命令,说明她暂时在谢府是安全的。
可一旦皇后知晓她刚打个照面就把人拿下了,还不以为她狐狸精转世,把谢烬迷得五迷三道,顿时给她来个刺杀的懿旨,估计她也离死不远了。
香茗小跑回来,把纸铺在姜月怜的面前,已经迫不及待等待姜月怜的回答了。
然而,姜月怜是谁?
岂能轻易被她拿捏?
她弱柳扶风地往桌子上一趴,眉心紧紧皱着,一只手还不停揉肚子。
五脏六腑也很给面子的在这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
姜月怜做戏做全套,好似强忍着饥饿,一把握住笔杆,艰难地在纸上画了个大大的“一”字。
香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夫人您这写的是什么啊?”
姜月怜虚弱的跟马上就要嘎了似的,委屈巴巴地抬眸望着香茗,眼眶微红。
“你!你倒是继续啊?”
“算了。”香巧终于看懂姜月怜想表达的意思,“香茗,先给夫人布膳,待夫人吃饱了,该咱们知道的一个也不会漏了。毕竟,皇后娘娘还等着呢。”
最后一句显然是对姜月怜的威胁,但姜月怜不在乎。
皇后和谢烬的脸色她受着也就受了,两个丫鬟也想对她指手画脚?
垂眸坐在椅子上,姜月怜放下手中的笔,一脸等待的神情。
香茗深吸了口气,强忍下心中的愤愤,才去布膳。
吃饱喝足,总令人昏昏欲睡。
姜月怜歪着身子靠在贵妃榻上,眼皮渐渐下沉。
每当眼皮合拢的时候,眼前总会浮现谢烬那双阴鸷的面孔。
她不相信谢烬从前不知那名婢女是奸细。
可偏偏选择在他面前用那么残忍的方式要了婢女的命,姜月怜知道谢烬是做给她看的。
前有心狠手辣的谢烬,后是诡计多端的皇后。
姜月怜觉得自己是颗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小白菜,怎么走都会步入深渊。
“夫人,别怪奴婢没提醒你,皇后娘娘可是在宫中等着回话的。”
香茗憋了一肚子火,含着对张管家的怨气,一整晚都没睡好。
这会儿姜月怜还有心思打盹儿?
真把自己当成飞上枝头的主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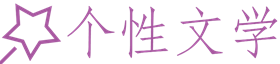 个性文学
个性文学